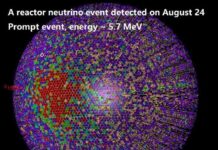中新社杭州5月7日電 題:傳世宋畫《秋蘆飛鶩圖》首次從海外回鄉展覽有何意義?
——專訪浙江省博物館原館長陳水華、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任史明理
作者 嚴格 林波 曹丹
宋代是中國繪畫的巔峰時期,其繪畫作品高度的寫實性與高超的表現技藝令人讚嘆。在這一時期,花鳥畫橫空出世,以逼真自然的藝術特色獨樹一幟。
2024年底至2025年初,浙江省博物館“問羽:宋代的自然與藝術世界”展(下稱“問羽”展)匯集了來自海內外8家收藏機構的15幅宋代花鳥畫真跡,並藉助科技手段,帶領民眾“走進”畫中世界。
宋代花鳥畫有何藝術特色?“外眼”如何看待宋代花鳥畫?向海內外收藏機構借用展品,對推動中外文化交流有何意義?
浙江省博物館原館長、鳥類生態學博士陳水華,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任、中國藝術策展人史明理(Clarissa von Spee)近日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獨家專訪,對此作出解讀。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:
中新社記者:宋代花鳥畫有何藝術特色?
陳水華:花鳥這一題材,起初祗是人物畫的裝飾元素,而作為獨立畫科,大概萌芽於南北朝時期。《唐朝名畫錄》記載的花鳥畫家有20多人,其中薛稷畫鶴最為精妙,邊鸞畫孔雀技法嫻熟。
五代十國時期,花鳥畫在西蜀和南唐突然興盛,出現明顯的風格分野,即黃筌的“黃家富貴”和徐熙的“徐熙野逸”。不過,二者的畫作都展現出高度的寫實性。
到了宋代,在偏愛且擅長花鳥畫的宋徽宗趙佶帶領下,宋代畫家不僅繼承了黃筌以來北宋畫院寫生的傳統,還將“格物窮理”的美學追求推向了極緻。
據記載,畫院畫家在描繪孔雀升墩時,宋徽宗對所有作品都不滿意。因為宋徽宗說,孔雀升墩時總是先抬左腳,而眾畫家筆下的孔雀卻都以右腳為先。
徽宗時期,畫院花鳥畫形成的準確細膩、合乎物理的寫實風格,被稱為“宣和體”。“宣和體”的藝術風格可概括為:形象的寫實性、詩意的含蓄性和法度的嚴謹性,這一追求甚至影響了整個宋代畫壇。
我曾系統翻閱《宋畫全集》,在174幅宋代花鳥畫中確認了67種鳥類。這些畫中的鳥類大多數能被精準辨識到物種,宋畫的高度寫實性與高超的表現技藝,實在令人驚嘆。
中新社記者:美國觀眾是如何看待以《秋蘆飛鶩圖》為代表的宋代花鳥畫的?
史明理:美國博物館的觀眾將中國畫視作中國文化的歷史瑰寶,它們與西方藝術作品有著本質的區別。其中,宋代花鳥畫尤其受歡迎,觀眾著迷於作品的高度寫實性,以及畫家精湛的水墨技法。此外,當美國觀眾得知該作品是繪製在絹上時,都驚嘆不已。

以《秋蘆飛鶩圖》為例,這幅畫作由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於1984年從日本大阪購入,其收藏歷史可追溯至17至19世紀統治日本的德川家族。
該畫作描繪了喜鵲、燕子和鴛鴦三種鳥類。燕子屬於候鳥,中國東晉時代的詩人陶淵明曾在詩中寫道:“翩翩新來燕,雙雙入我廬。先巢故尚在,相將還舊居”,生動記錄了燕子在暮春時節返巢、深秋之際離去的景象。
正如“問羽”展呈現的,宋代花鳥畫家深受當地自然美景的啟發,在感受四季更迭的同時,對鳥類的行為、其與氣候的關係也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觀察。
梁楷被認為是《秋蘆飛鶩圖》的創作者,南宋時期他曾任畫院待詔,性情豪放,不拘泥於禮法,被視為一個從院畫向禪畫過渡的畫家。其粗放的“減筆畫”極富創造性,開創了中國畫水墨寫意畫法的新局面。
《秋蘆飛鶩圖》採用了一角式構圖法,即在畫面一側留出大片空白。這一技法是13世紀前後,居住在杭州及周邊的梁楷等宮廷畫家與禪宗畫家常用的。此類構圖手法以簡潔、單色的線條運用,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並契合了禪宗“萬物皆為幻象”的理念。
中新社記者:以梁楷為代表的“寫意派”宋代畫家是如何體現“科學精神”的?
陳水華:寫生追求形似,寫意追求傳神。一幅花鳥作品,若能做到形神兼備,應當算是上品。
久居杭州的梁楷是宋代畫家中的傳奇人物。世人對他的人物畫《潑墨仙人圖》較為熟悉,但他的寫意花鳥畫同樣精彩,被各地博物館廣泛收藏。
此次展出梁楷的兩幅作品——《秋蘆飛鶩圖》《疏柳寒鴉圖》,分別被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,“問羽”展是這兩幅畫作首次一同回到杭州展出。
兩幅畫作筆法簡約、嫻熟且精準,堪稱減筆水墨寫意畫的精品。雖然畫風簡約,但畫中鳥類特徵鮮明,都可精準辨識到物種。《秋蘆飛鶩圖》中繪有喜鵲、金腰燕和綠頭鴨,《疏柳寒鴉圖》所描繪的鳥類則是達烏裡寒鴉。
金腰燕是家燕的姐妹種,其外形特徵顯著,後腰部呈金黃色,在飛行時尤為明顯,易於分辨。在繪畫表現中,但凡後腰呈淺色的,即為金腰燕,反之則是家燕。
在這兩幅減筆水墨寫意畫中,所繪鳥類都抓住了鳥類的形態特徵,而且也符合它們與環境和季節的關係,展現出宋代畫家遵循科學規律、注重“寫實”的一面。
中新社記者:向海內外的收藏機構借用展品,對推動中外文化交流有何意義?
陳水華:在中國文博界,借單件文物其實比借整個展覽難度更大。宋畫分散在世界各地,此次籌備“問羽”展時,我們向海內外多家博物館廣發邀請函。
然而,借展過程困難重重。部分書畫作品因處於休眠期,出於文物保護考慮無法出借;受內部流程等因素制約,還有些文物需要提前提交申請;此外,一些海外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家對浙江省博物館還不够瞭解,最終未能借到展品。但我認為,無論成功與否,整個借展過程就是一種交流。
此次,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將梁楷的《秋蘆飛鶩圖》和李迪的《宿禽激湍圖》兩幅畫作借給我們,對此我們深表感謝。這份信任都源於他們對我們前期工作的肯定。
我相信,“問羽”展的成功舉辦是一個好的開端,能讓更多海內外收藏機構看到浙江省博物館在前期溝通、畫作布展、展品歸還等方面展現出的專業性,以及民眾對文物的欣賞熱情,從而推動更多的交流合作。
史明理:這是我們博物館所藏的宋代花鳥畫首次在中國展出。
我認為,任何文明的藝術作品都是“文化使者”,它們承載著創作者的思想與所處時代的文化,見證了特定時期的社會狀況,能够激發當代人對創作者及其所代表文化的尊重。
基於此,藝術作品實際上肩負著獨特的“外交使命”。博物館通過舉辦展覽,激發各國民眾對文物的認識,幫助他們瞭解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,這在喚起觀眾好奇心、傳播知識、推動文化交流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。正因如此,中外博物館之間開展文物借展交流活動,意義深遠。(完)
來源中新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