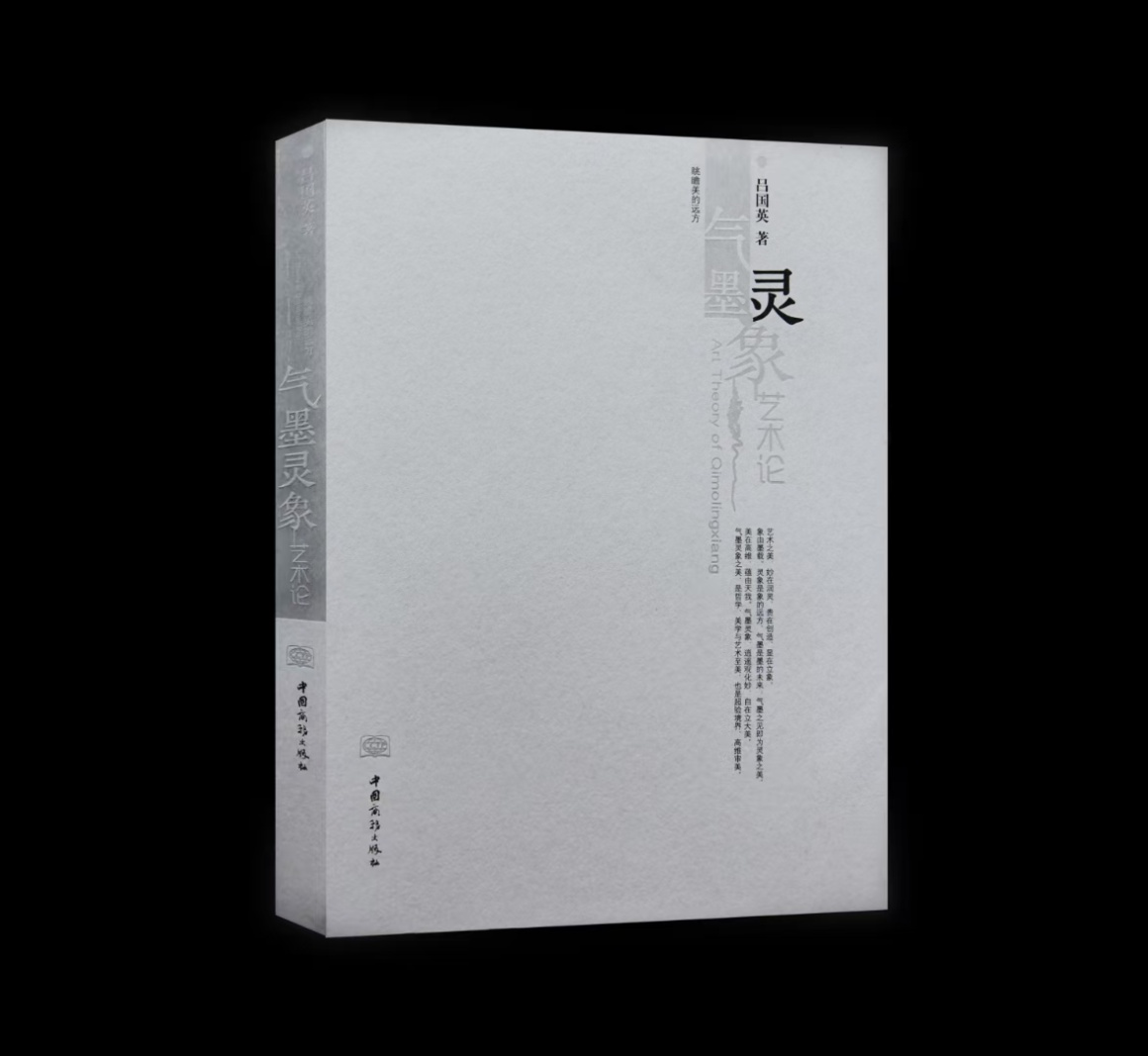“氣墨靈象”論的藝術革命
——解構呂國英的墨學新體系
艾 慧
1 “氣墨”概念的理論內涵與歷史座標
呂國英提出的“氣墨”概念,絕非簡單的物質性顏料或技法指稱,而是一個融合哲學、美學與藝術史維度的革命性範疇。從文字學溯源,“氣”的甲骨文原形為“三橫”,上方一橫代表宇宙混沌初始,上下兩橫合為天地,中間短橫則象徵天地間流動的元氣;而“墨”從黑從土,自古被視為“萬色之母”,具有深邃的文化積澱。二者結合形成的“氣墨”,既保留了物質的實體性,又昇華至精神層面,成為連接宇宙本源與藝術表達的媒介。呂國英對此有精闢界定:“氣墨,既為氣之墨,亦為墨之氣;是氣墨一體,也為墨氣合一;既構建一種筆墨之態,又表達一種筆墨境界”。
在藝術史脈絡中,氣墨被定位為筆墨演進的終極未來。呂國英建構了一套清晰的墨象演進譜系——
線墨階段:對應具象藝術,以線性描摹物象輪廓,隨物移形,如早期工筆劃技法;
意墨階段:孕育意象藝術,通過筆墨寄託主觀情志,如文人畫的寓意傳統;
潑墨階段:催生抽象藝術,突破形的束縛直達心緒表達,見於大寫意極致化創作;
樸墨階段:呈現真象藝術,追求樸拙、樸質、樸真的美學境界;
氣墨階段:矗立靈象藝術,抵達藝術語言的至美高峰。
表:呂國英筆下的墨象演進五階段
墨的形態 承載之象 核心特徵 代表技法
線墨 具象 工藝描摹,求形狀貌 工筆線描
意墨 意象 寓意寄情,心志表達 文人寫意
潑墨 抽象 心緒宣洩,超越形似 潑墨大寫意
樸墨 真象 樸拙真率,去偽存真 金石用筆
氣墨 靈象 天人合一,自由超越 氣化筆墨
尤為重要的是,氣墨對傳統筆墨觀實現了三重超越:其一,它打破“筆墨中心主義”的桎梏——自明代董其昌提出“以筆墨之精妙論,則山水決不如畫”,經清代“四王”推至“作畫第一論筆墨”的極端化,筆墨漸成僵化程式;其二,它回應了現代藝術家的“筆墨憂患”——如傅抱石呼籲“思想變了,筆墨就不能不變”,吳冠中質疑“脫離了具體畫面的孤立的筆墨,其價值等於零”;其三,它超越了20世紀三次筆墨論爭(中國畫改良論、窮途末路論、筆墨等於零論)的理論困境,為筆墨發展提供了新範式。
2 藝術史語境中的定位:對筆墨危機的回應
呂國英提出氣墨論,直指中國繪畫積弊四百年的筆墨危機。他犀利指出當下筆墨存在六大痼疾:“陳”即陳舊腐朽,因循守舊;“俗”即諂媚逢迎,迎合低級趣味;“髒”即污濁齷齪,缺乏雅正;“假”即虛情假意,喪失真誠;“亂”即混雜無序,技法混亂;“死”即呆板僵硬,毫無靈動。其中“死”為萬惡之源,其病根在於筆墨的程式化、僵化、概念化,導致中國書畫“千篇一律、千人一面”,創造力衰竭。
這種危機在全球化語境中更顯緊迫。20世紀初的“西畫東漸”浪潮中,徐悲鴻、林風眠等留歐藝術家引入西方藝術體系,本意是改良中國繪畫,但因當時中國積貧積弱、文化自信低迷,西方藝術被奉為“仰高”神聖,導致中國繪畫陷入身份認同困境。呂國英深刻指出:“無不與近代以來,由於中國長期積貧積弱、藝術漸以頹敗,國民尤其是藝術中人,缺乏甚至沒有了文化與藝術自信不無關係”。
面對這種雙重危機(內在僵化與外來衝擊),氣墨論提供了破局之道:它既回歸中國藝術本源——追溯至宇宙元氣與生命精氣的哲學維度;又保持開放融合姿態——不排斥西方藝術精華,而是將其納入墨象演進的大框架中。如林風眠的光影彩墨、吳冠中的形式抽象,在氣墨論中都被視為墨象發展的合理階段,而非對立物。
3 氣墨與靈象的辯證關係:藝術本體的重構
氣墨論的核心突破在於其與“靈象”構成的辯證統一體。呂國英創造性地提出:“‘氣墨’‘靈象’形質一體、不可分割,且互為形式內容”。這一命題徹底解構了傳統藝術理論中形式與內容的二元對立——
從創作過程看:氣墨為材質載體(形式),靈象為藝術呈現(內容)。氣墨是“技、器、巧”,是“理念、思想、法則、靈魂”;靈象則是“生命之象、靈魂之象、神聖之象”,是“正象、真象、善象”。
從審美境界論:二者關係發生反轉——靈象成為精神本體(內容),氣墨則成為其物化形態(形式)。靈象指向“純粹之象、自由之象、超驗之象”,是“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之象”;而氣墨則是這種境界的“顯影劑”。
呂國英通過一個精妙比喻揭示其關係:正如大火箭承載重物飛向深空,射電望遠鏡捕捉宇宙信號,量子衛星實現超距傳輸,高端載體拓展人類認知邊界;同理,氣墨作為藝術載體的革命,使表現“靈象”這種高維審美成為可能。他斷言:“人類文明史,一定意義上,就是一部不斷創制工具、發現與應用載體的歷史。科學探索如此,文藝創作亦然”。
這種互為形式內容的理論,實質是對藝術本體論的重構。它既否定“筆墨至上”的形式主義,也批判脫離載體的虛無主義,確立了一種迴圈互生的藝術哲學:氣墨因承載靈象而獲得意義,靈象因氣墨承載而得以顯現。如呂國英所言:“‘靈象藝術’即為‘氣墨繪畫(創作)’,‘氣墨繪畫(創作)’亦為‘靈象藝術’”。
4 理論價值與批評實踐:四維一體的學術貢獻
呂國英的氣墨論構建了一個四維一體的理論體系,具有多重學術價值——
本體論創新:提出“藝法靈象”是藝術的本質規律,將藝術本質定位於矗立審美境界。藝術法則分層次:“藝法具象是藝術的相對規律,藝法意象、抽象是更高一級的藝術相對規律,藝法靈象就是藝術的遠方規律”。
藝術史觀重構:打破中西藝術對立的敘事模式,將中國筆墨演進與西方藝術流派納入同一演化邏輯。從原始美術、古典美術到現代藝術、後現代藝術的演進,與線墨到氣墨的發展具有同構性。
批評標準重建:針對當下藝術亂象(如“波普藝術”對紅色經典的惡搞、“豔俗藝術”的低俗趣味、“擬象藝術”的複製抄襲),提出“五忌”原則:忌滯、忌退、忌濫、忌抄、忌醜,為藝術評價提供清晰尺度。
創作方法論:主張藝術作品需具“五尚”特質——尚絕(原創惟一)、尚新(包前孕後)、尚進(時代高度)、尚融(跨文化和諧)、尚極(完美極致);藝術家須備“五崇”修養——崇學(博學融通)、崇德(品格擔當)、崇靜(心性純淨)、崇變(創新求變)、崇論(理論自覺)。
在批評實踐層面,氣墨論直指當下文藝創作困境。呂國英指出,文學領域陷入“低俗文學”漩渦,審美理想被消蝕;美術界則充斥“淺薄藝術”,部分創作者“靠虛名糊塗亂抹、愚弄受眾、瘋狂斂財”。其病根在於筆墨(廣義藝術語言)淪落至“自然境界與功利境界之間”,而氣墨論則為文藝攀登“天地境界”(馮友蘭哲學範疇)提供路徑。
5 創新與商榷:對氣墨論的三重思辨
呂國英的氣墨論雖具開創性,但也存在值得商榷的空間,主要體現在三方面——
5.1 超驗性的可操作性
氣墨靈象被描述為“超驗境界”,呂國英借維特根斯坦之言區分“經驗語言”與“超驗語言”,坦言:“經驗世界的事物都可說,而且都能夠說清楚;超驗世界的事物不可說,應該保持沉默”。這固然賦予理論哲學深度,但具體創作中如何實現“氣化之墨”?是否可能陷入玄學化困境?雖然呂國英強調“氣墨”包含物質性(水墨、油彩等載體),但其至高境界的模糊性仍可能削弱理論指導性。
5.2 歷史決定論色彩
墨象五階段演進模型(線墨→意墨→潑墨→樸墨→氣墨)具有強烈的歷史目的論傾向。藝術發展是否必然線性進化?回溯藝術史,宋代院體畫(線墨)與明清寫意畫(意墨、潑墨)實為並行脈絡,非簡單取代關係。將氣墨定位為“迄今可預見的最高形式”,可能忽略了藝術演進的多元複雜性。
5.3 跨文化適用邊界
儘管理論吸收西方藝術元素(如肯定趙無極、朱德群融合實踐),但“氣”的概念根植於中國宇宙觀(元氣論),與西方摹仿說、表現論存在哲學基礎差異。當應用於非水墨藝術(如油畫、裝置)時,“氣墨”的闡釋效力可能減弱。如呂國英所言:“氣墨之氣,是墨之靈;氣墨之墨,為氣之魂”,這種氣靈墨魂的轉換在油畫中如何實現?仍需具體案例驗證。
6 結論:墨學新體系的當代意義
呂國英的“氣墨論”代表中國藝術理論從“傳統話語現代轉化”到“自主體系建構”的關鍵躍遷。其價值不僅在於提出新概念,更在於構建了一個本體論、認識論、方法論統一的完整體系:在本體論上,以“氣墨靈象”重新定義藝術本質;在認識論上,以墨象演進重構藝術史觀;在方法論上,以“五尚五崇”指引創作實踐。
面對中國藝術發展的深層矛盾——既要掙脫四百年的筆墨桎梏,又要在全球化中確立文化主體性——氣墨論提供了超越二元對立的解決方案。它既不退回“筆墨神聖”的保守立場,也不墮入“筆墨等於零”的虛無主義,而是以螺旋上升的辯證思維,將傳統筆墨提升至氣化境界,為中國藝術的未來矗立了精神座標。
正如大火箭升空需突破重力束縛,藝術創新亦需掙脫歷史慣性與文化焦慮。呂國英寄望氣墨靈象能“還如今混亂無序、動盪不安的世界,一個審美的時空、一個精神的遠方”。在築就文藝高峰的時代使命下,這一理論的意義已超越技法層面,成為中華美學精神現代轉化的重要路標。其爭議處,恰是學術生長點;其未完成性,正是未來探索的空間。
(論文原文載:《解放軍報》長征副刊、《文藝報》《人民政協報》學術家園、《“氣墨靈象”藝術論》·中國商務出版社;《粵海風》《中華時報》理論連載等)
2025.02.18·北京
附
呂國英 簡介
呂國英,文藝理論、藝術批評家,文化學者、詩人、狂草書法家,原解放軍報社文化部主任、中華時報藝術總監,央澤華安智庫高級研究員,創立“氣墨靈象”美學新理論,建構“哲慧”新詩派,提出“書象·靈草”新命題,抽象精粹牛文化。出版專著多部、原創學術論文多篇,撰寫哲慧詩章兩千餘首。
主要著作:《“氣墨靈象”藝術論》《大藝立三極》《未來藝術之路》《呂國英哲慧詩章》《CHINA奇人》《陶藝狂人》《神雕》《國學千載“牛”縱橫》《中國牛文化千字文》《新聞“內幕”》《藝術,從“完美”到“自由”》。
主要立論:“靈象”是“象”的遠方;“氣墨”是“墨”的未來;“氣墨”“靈象”形質一體、互為形式內容;“藝法靈象”揭示藝術終極規律;美是“氣墨靈象”;“氣墨靈象”超驗之美;“書象”由“象”;書美“通象”;“靈草”是狂草的遠方;詩貴哲慧潤靈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