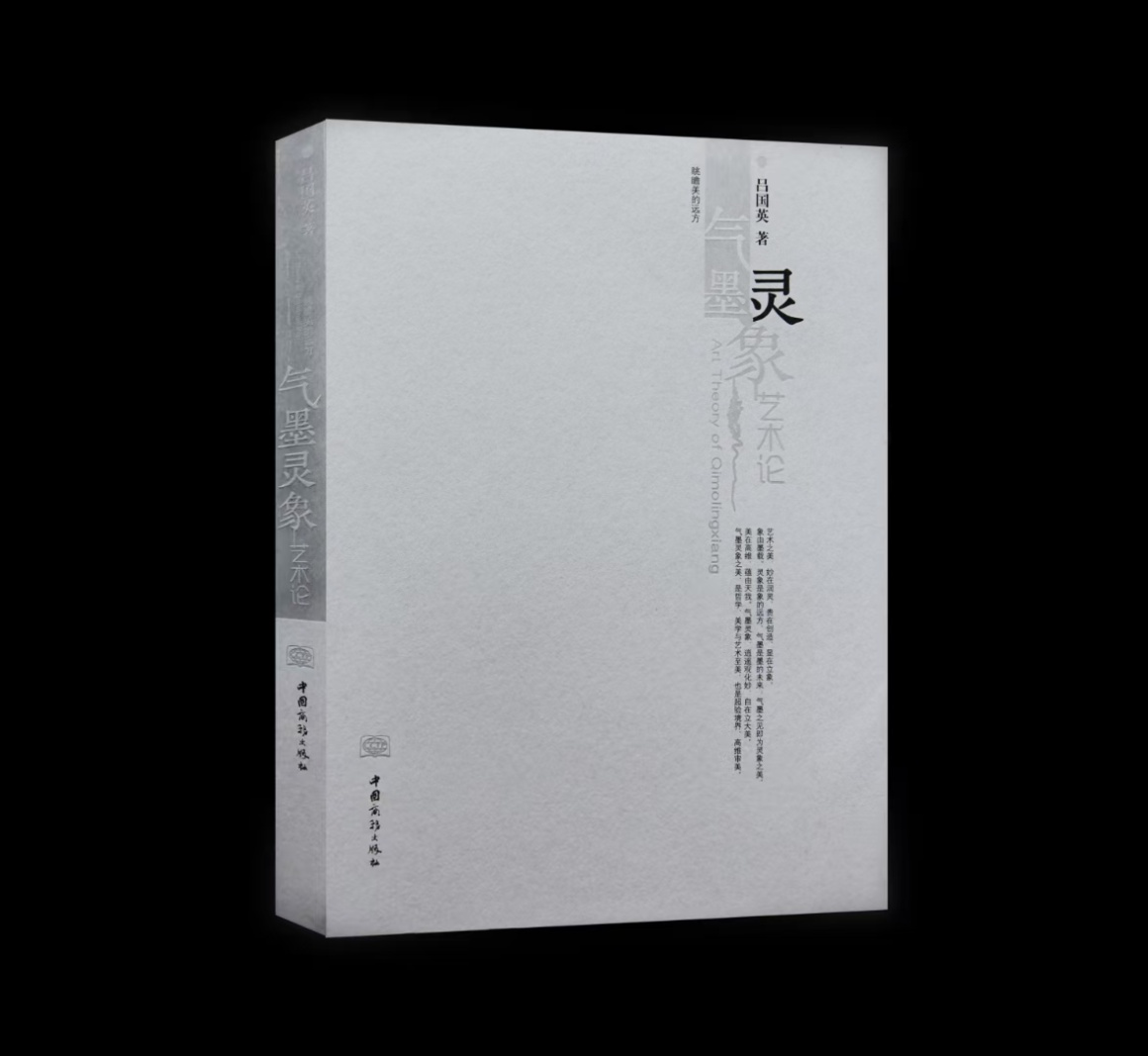“氣墨靈象”的藝術哲學
——呂國英藝術論的形式革命與本體超越
艾 慧
在當代中國藝術理論領域,呂國英提出的“氣墨靈象”藝術論以其獨特的理論建構和深刻的美學洞察引發了廣泛關注。這一理論不僅試圖解決中國藝術發展中的核心難題,更在哲學層面重新定義了藝術創作與審美的本質關係。本文將從理論內涵、歷史語境、創新價值等維度,對《“氣墨”“靈象”互為形式內容——“氣墨靈象”核心立論之三》一文進行深度解讀,揭示其在當代中國藝術理論發展中的里程碑意義。
1 理論核心與體系定位:形式與內容的辯證統一
呂國英“氣墨靈象”藝術論的核心命題直指藝術哲學的基本問題——形式與內容的關係。在《“氣墨”“靈象”互為形式內容》中,呂國英創造性地提出:“‘氣墨’與‘靈象’形質一體、不可分割,且互為形式內容,呈現融合大美,矗立終極藝象”。這一論斷超越了傳統藝術理論中形式與內容的二元對立,建立了辯證統一的藝術本體論。
“氣墨”概念解析:在呂國英的理論體系中,“氣墨”被定義為“筆墨的未來”,是墨的化境與超越。它從線墨、意墨、潑墨、樸墨發展而來,既是物質的繪畫媒介,又是精神性的藝術表達。“氣墨”既為‘氣之墨’,亦為‘墨之氣’;是氣墨一體,也為墨氣合一;既構建一種筆墨之態,又表達一種筆墨境界;是筆墨演進的終極性未來,也是大美藝象的極致性載體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這裏的“墨”不僅是具體的水墨、油彩等物質材料,更是包括創作主體、環境、過程等所有創作元素的總稱。
“靈象”概念解析:與“氣墨”相對應,“靈象”則是“象的遠方”,是藝術之象發展演進的終極形態。“靈象從具象、意象、抽象、真象(樸象) 走來;象由墨生,墨因象載;靈象,既為靈之象,又為象之靈;是靈象一體,亦為象靈合一;既展示一種象之形態,又呈現一種象之境界”。靈象的本質是生命之象、靈魂之象、神聖之象,是正象、真象、善象,是純粹之象、自由之象、超驗之象。
呂國英理論最精妙之處在於揭示了“氣墨”與“靈象”的互文關係:“氣墨是靈象的筆墨,靈像是筆墨的氣墨”。這意味著在藝術創作的高維境界中,形式即內容,內容即形式,二者如陰陽相生,不可分割。這種關係類似於中國哲學中的“體用不二”,也呼應了西方現象學“形式-內容”一元論的觀點,但在藝術領域提出了全新的理論範式。
表:呂國英“氣墨靈象”理論的核心概念體系
概念 定義 演進歷程 本質特徵
氣墨 筆墨的未來 線墨→意墨→潑墨→樸墨→氣墨 氣墨一體、墨氣合一、大美載體
靈象 象的遠方 具象→意象→抽象→真象→靈象 靈象一體、象靈合一、大藝大美
氣墨靈象 藝術終極形態 形式與內容的辯證統一 互為形式內容、形質一體、融合大美
從理論體系定位看,該文是《“氣墨靈象”藝術論》的第三篇核心立論,與首篇《逸形入靈 大藝立象》(聚焦“靈象”)、次篇《如氣化墨 載靈承象》(聚焦“氣墨”)共同構成三位一體的理論架構。在這個體系中,“氣墨靈象”不僅是一個藝術概念,更是一個哲學命題,指向藝術創作與審美的終極境界——超驗自由的精神實現。
2 歷史語境:筆墨論爭的脈絡梳理
呂國英的理論建構建立在對中國繪畫史上筆墨論爭的深刻反思之上。在《“氣墨”“靈象”互為形式內容》一文中,他系統梳理了四百餘年中國繪畫的筆墨觀念史,揭示了“氣墨靈象”理論提出的歷史必然性。
2.1 筆墨觀念的三大歷史階段
“筆墨至上”論(明清):以董其昌、陳繼儒及清“四王”(王時敏、王鑒、王原祁、王翚)為代表,將筆墨技巧神聖化。董其昌斷言:“以筆墨之精妙論,則山水決不如畫”;陳繼儒強調:“文人之畫,不在途徑,而在筆墨”;王學浩更在《山南論畫》中開宗明義:“作畫第一論筆墨”。這種觀念導致筆墨的程式化和僵化,使藝術創作陷入泥古不化的困境。
“筆墨反思”論(清初至近代):以石濤為代表,對筆墨至上進行批判性反思。石濤在《苦瓜和尚畫語錄》中提出:“筆墨當隨時代,猶詩文風氣所轉”,並強調“我之為我,自有我在……我自用我法”。石濤的反思揭示了筆墨應隨時代創新、表達個性的本質要求,但未能改變主流畫壇的保守傾向。
“筆墨憂患”與“筆墨無用”論(現當代):以傅抱石、石魯、吳冠中等大家為代表。傅抱石感喟:“思想變了,筆墨就不能不變!”;石魯豪語:“思想為筆墨之靈魂”;吳冠中則提出更具顛覆性的觀點:“脫離了具體畫面的孤立的筆墨,其價值等於零”。這些觀點直指筆墨的形式主義危機,但未能建立新的理論體系。
2.2 三次重大論爭的理論困境
呂國英尖銳指出,20世紀中國美術界的三次重大筆墨論爭——20世紀初的“中國畫改良論”之爭、1980年代的“中國畫窮途末路論”之爭、1990年代的“筆墨等於零”與“守住中國畫底線”之爭——均陷入理論貧乏的困境:“三次論爭基本是就筆墨論筆墨,皆無最終或建設性結論,甚至成為一種‘公婆’論、‘混’論,根本之原因在於沒有進入理論層面,沒有提出關於筆墨之新觀點、新立論”。
這種理論貧乏的直接後果是中國繪畫長期受困於筆墨痼疾,表現為陳、俗、髒、假、亂、死“六字病症”,其中“死”是根本問題,即筆墨的程式化、僵化、概念化。呂國英認為,這些問題的本質是藝術本體論迷失——將筆墨視為目的而非載體,忽視了“墨為象載,象為墨承”的藝術本質。
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,“氣墨靈象”理論的提出具有革命性意義:它超越了傳統筆墨論爭的非此即彼,從藝術本體高度重建了筆墨與意象的關係,將中國藝術理論推向新的哲學維度。
3 藝術史座標:演進規律與終極形態
呂國英的“氣墨靈象”理論不僅是對歷史問題的回應,更是對藝術發展規律的深刻揭示。他將藝術史解讀為“墨”與“象”互動演進的辯證過程,建構了完整的藝術史觀和未來學框架。
3.1 “五墨五象”的演進圖譜
在呂國英的理論中,藝術形式的演進呈現為清晰的階段性規律——
墨的進階:從線墨(工藝描摹之墨)→意墨(寓意寄情之墨)→潑墨(心性放縱之墨)→樸墨(樸拙真質之墨)→氣墨(天人合一之墨)。這是一個從技術狀態到藝術情態再到天地境界的昇華過程。
象的層進:從具象(物象輪廓)→意象(心意情態)→抽象(心緒表達)→真象(三象合一)→靈象(超驗自由)。這是一個從形而下的物象描摹到形而上的精神顯現的超越過程。
這種雙重演進並非機械對應,而是辯證統一:“線墨繪畫·具象藝術與意墨繪畫·意象藝術之別,也有了潑墨繪畫·抽象藝術與樸墨繪畫·真象藝術之異,也自然有氣墨繪畫·靈象藝術之論”。每一階段的“墨”承載相應層級的“象”,共同構成藝術發展的歷史鏈條。
3.2 終極藝術形態的超驗性
在藝術演進的頂端,“氣墨靈象”代表了迄今可預見的最高藝術形式:“是墨象藝術的高峰,是藝術語言的至美之象”。這一形態具有三大超驗特徵——
時空融合性:氣墨靈像是“諸‘墨’在創作主體的‘喚醒’‘為一’與運化中所‘呈現’出的‘審美情態’‘精神狀貌’與‘至美境界’”,實現了創作主體與表現媒介的完全融合。
生命整全性:靈象藝術呈現“生命之象、靈魂之象、神聖之象”,是“正象、真象、善象;是純粹之象、自由之象、超驗之象”,體現了藝術對生命本真的回歸。
審美自由性:氣墨靈象境界中,審美成為“芸芸眾生每一個人都應該享有的特殊自由與特別權利”,是人“實現自我救贖”的精神通道。這種自由不是逃避現實,而是對現實的精神超越。
呂國英特別強調,氣墨靈象不是“1+1又+1再+1等於4”的簡單疊加,而是諸藝術元素在高維審美境界中的有機整合。它既是藝術史演進的理論終點,也是藝術家實踐的無盡征程。
4 實踐啟示:創作與審美的雙重超越
“氣墨靈象”理論不僅是藝術哲學的本體論建構,更為藝術創作與審美實踐提供了具體路徑。呂國英從創作法則、藝術家修養、審美境界等維度,構建了完整的實踐體系。
4.1 創作法則:“藝法靈象”的根本規律
呂國英提出“藝法靈象”命題,將其視為藝術的本質性規律:“藝法靈象就是藝術的根本性規律,這種本質性規律,體現為藝術的終極性引領與根本性遵循”。這一命題包含三層實踐指引——
本體論層面:藝術的本質意義在於矗立審美,塑形立像是實現這一本質的基本功能。
認識論層面:藝與術存在辯證聯繫——藝為美,術為技,二者殊途但最終同歸。
方法論層面:藝術法則分屬不同層次,“藝法具象是藝術的相對規律,藝法意象、抽象是更高一級的藝術相對規律,藝法靈象就是藝術的遠方規律”。
“藝法靈象”的提出,為藝術創作確立了終極價值座標。它要求藝術家超越對具體技法的執著,以呈現“靈象”為根本追求,這既是藝術創作的最高法則,也是突破當下創作困境的根本路徑。
4.2 藝術家修養:“高學大德”的必然要求
呂國英深刻指出,進入氣墨靈象創作境界的關鍵在於藝術家的內在修養:“‘高學大德’者方入‘氣墨靈象’之境”。這一要求包含兩個維度——
學養維度:“學即學養,是博學之學,是歷史、人文之積學為成者”。呂國英引用恩格斯對文藝復興的評價,強調博學是“巨人時代”的特徵,中國藝術史同樣證明“歷史上哪位藝術大家不是學富五車,又哪一位不為才高八斗?”。在當代語境中,這種學養更需具備跨文化視野,融合國學根基與世界主流文化認知。
德性維度:“德即德養,是德行、品位修行之要義,更是責任、擔當之根本”。呂國英引用習近平總書記講話強調:“偉大的文藝展現偉大的靈魂,偉大的文藝來自偉大的靈魂”。藝術家須“有大德之養”,在思想道德修養上追求卓越,抵制炫富競奢、低俗媚俗、見利忘義等陋行。
這種“崇學崇德”的修養論,將藝術家的精神境界視為創作突破的先決條件,呼應了中國傳統“畫如其人”的藝術觀,也為當代藝術家的自我提升指明了方向。
表:藝術家進入氣墨靈象境界的“五崇”要求
要求 內涵 實踐指向 終極目標
崇學 博學融通 國學為本,兼通世界文化 學養深厚,才高八斗
崇德 德性修養 抵制低俗媚俗,擔當社會責任 行為世範,德藝雙馨
崇淨 心性純淨 去除雜念,專注藝術本真 精神清靜,一塵不染
崇變 創新求變 突破陳規,隨時代而變 我自用我法,不拘古法
崇論 理論自覺 反思藝術本質,建構理論思維 知行合一,理藝互證
4.3 審美境界:“潤靈樂境”的普世價值
在審美層面,呂國英提出“潤靈樂境”概念,強調氣墨靈象具有普世審美價值:“審美決非藝術家的專利,而是芸芸眾生每一個人應該享有的自由與權利”。這種審美境界具有三重特徵——
主體解放性:當主體進入“氣墨靈象”狀態或“天人合一”“天我為一”境界時,就能“感知與體悟‘大美’之存境”,實現“身心的解放”和“生命的愉悅”。
自我救贖性:在氣墨靈象的審美體驗中,人能夠“自由出入世俗與審美之中”,實現“審美理想中的自我,完成了自我救贖”。這一觀點將藝術審美提升到存在論高度,賦予其精神救贖的功能。
跨媒介普適性:氣墨靈象之美“可以是文學、戲劇,也可以是曲藝、書法,還可以是音樂、舞蹈,又可以是電影、電視、美術、民間文藝、群眾文藝等”。這種普適性使理論超越具體藝術門類,成為普世美學原則。
呂國英特別強調,氣墨靈象的審美境界需要通過“推挽”機制實現——藝術家創作氣墨靈象作品“推”動受眾審美境界提升,而受眾的高維審美需求又“挽”引藝術家創作更高境界的作品。這種互動關係為藝術高峰的築就提供了動力學解釋。
5 學術創新:方法論突破與體系建構
“氣墨靈象”理論在藝術哲學領域實現了多重突破,其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——
5.1 範式革命:從二元對立到辯證統一
呂國英理論最根本的創新在於顛覆了形式與內容的傳統二元論。在藝術史上,形式與內容的關係長期處於對立狀態:從董其昌的“筆墨至上”(形式主義)到吳冠中的“筆墨等於零”(內容優先),都未能解決這一根本矛盾。而“氣墨靈象”理論創造性地提出:“氣墨是靈象的筆墨,靈像是筆墨的氣墨”,建立了形式與內容的辯證同一性。
這一命題具有深刻的哲學內涵:在藝術的高維境界中,媒介(墨)與表現(象)不再是承載與被承載的關係,而是互為本體、互為顯現。這種思想既根植於中國哲學的“體用不二”觀,又呼應了海德格爾“藝術是真理自行置入作品”的存在論美學,為藝術本體論提供了新的解釋框架。
5.2 跨文化融合:本土話語的現代轉化
在方法論上,呂國英實現了中國藝術話語的現代轉化。他以“氣”“墨”“靈”“象”等中國傳統美學範疇為根基,通過現代性闡釋構建了既具民族特色又具世界意義的理論體系:
本土性根基:理論根植於中國藝術傳統,“筆墨論、氣象說,皆為獨具中國氣派的藝術理論範疇”。呂國英從文字學角度探討氣、墨、靈、象等概念,延續了中國文化的“六書”傳統。
現代性轉化:通過梳理林風眠、徐悲鴻的“中西結合”、趙無極、朱德群、吳冠中等“旅法三劍客”的融合實踐,理論實現了傳統筆墨與現代藝術表達的對接。
世界性視野:理論將氣墨靈象定位為“人類文明這精神世界演進的總概括、大哲思、高維美”,使中國藝術話語具備了普世解釋力。
這種跨文化融合不是簡單的“中西合璧”,而是立足本土傳統的創造性轉化,為中國藝術理論參與世界美學對話提供了範例。
5.3 體系性建構:邏輯閉環與開放拓展
“氣墨靈象”理論的另一重大創新是其嚴密的體系性。這一體系呈現出“閉合中開放”的特徵:
內在閉環性:理論以“問題發現(筆墨困境)→歷史分析(論爭梳理)→概念創新(氣墨靈象)→實踐路徑(藝法靈象/高學大德)→價值實現(潤靈樂境)”構成邏輯閉環。
外部開放性:理論框架具有延展性,如提出的藝術創作“五尚”(尚絕、尚新、尚進、尚融、尚極)、藝術家“五崇”(崇學、崇德、崇淨、崇變、崇論)、創作禁忌“五忌”(忌滯、忌退、忌濫、忌抄、忌醜)等,為後續研究預留了廣闊空間。
這種體系化建構使“氣墨靈象”理論超越了零散的畫論點評,成為具有嚴密邏輯結構的藝術哲學體系,在當代中國藝術理論建設中具有開創性意義。
6 結語:理論燭照下的藝術未來
呂國英的“氣墨靈象”理論以其深刻的歷史洞察、哲學高度和體系建構,為當代中國藝術發展提供了理論燈塔。這一理論的價值不僅在於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藝術界的筆墨之爭,更在於其指明了藝術創作與審美的未來方向——形式與內容在超驗境界中的辯證統一。
在當下藝術創作面臨諸多困境的背景下,“氣墨靈象”理論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:它要求藝術家擺脫對技巧程式的迷戀,超越中西對立的焦慮,以“高學大德”的修養追求“潤靈樂境”的審美理想。同時,理論對“靈象”的超驗性定位,也為藝術突破物質主義束縛、實現精神救贖提供了可能路徑。
當然,任何理論都有其歷史局限性。“氣墨靈象”理論在實踐操作層面的具體路徑尚需進一步探索,其超驗境界的普適性也有待更多藝術實踐驗證。但不可否認,呂國英的理論建構已為中國藝術開闢了一條通向高維審美的新道路。如他引用維特根斯坦所言:“凡是可說的,都能夠說清楚;凡是不可說的,就應該保持沉默”。或許,“氣墨靈象”的至美境界正在於其可說與不可說之間的玄妙平衡——這正是偉大藝術的永恆魅力。
(論文原文載:《解放軍報》長征副刊、《文藝報》《人民政協報》學術家園、《“氣墨靈象”藝術論》·中國商務出版社;《粵海風》《中華時報》理論連載等)
2025.03.12·北京
附
呂國英 簡介
呂國英,文藝理論、藝術批評家,文化學者、詩人、狂草書法家,原解放軍報社文化部主任、中華時報藝術總監,央澤華安智庫高級研究員,創立“氣墨靈象”美學新理論,建構“哲慧”新詩派,提出“書象·靈草”新命題,抽象精粹牛文化。出版專著多部、原創學術論文多篇,撰寫哲慧詩章兩千餘首。
主要著作:《“氣墨靈象”藝術論》《大藝立三極》《未來藝術之路》《呂國英哲慧詩章》《CHINA奇人》《陶藝狂人》《神雕》《國學千載“牛”縱橫》《中國牛文化千字文》《新聞“內幕”》《藝術,從“完美”到“自由”》。
主要立論:“靈象”是“象”的遠方;“氣墨”是“墨”的未來;“氣墨”“靈象”形質一體、互為形式內容;“藝法靈象”揭示藝術終極規律;美是“氣墨靈象”;“氣墨靈象”超驗之美;“書象”由“象”;書美“通象”;“靈草”是狂草的遠方;詩貴哲慧潤靈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