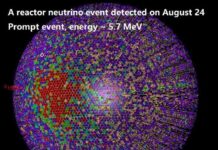中新社上海10月14日電 題: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如何相連?
——專訪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伯重
中新社記者 許婧
“世界中國學”對全球視野中的跨文化交流、文明互鑒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產生深遠影響。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舉行,與會中外學者圍繞“世界視野下的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”主題展開深入研討。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、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伯重日前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專訪,講述他眼中的世界中國學。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:
中新社記者:您認為“漢學”“國學”“中國學”三者概念有何不同?
李伯重:我認為世界中國學的核心,就是讓世界人民瞭解中國,讓中國人民把中國作為世界的一部分來瞭解。這些都需要由學術界提供比較好的知識作為支撐。過去20年,中國學研究新的動向已經出現了。
因為我在哈佛大學、密歇根大學、倫敦政治經濟學院、法國國家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等學校教過書,所以對歐美的中國研究有一些瞭解。我認為“國學”“漢學”可能都是一些比較陳舊的說法,準確來講應該是“中國學”。
“漢學”這個說法實際上只是在歐洲比較常見(英國除外),在美國很少見到。“漢學”研究範圍比較狹窄,主要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化思想和制度,集中於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。漢學研究有很大的成就,但是只靠漢學不能全面瞭解歷史中國,特別是難以瞭解中國重要的經濟活動、政治活動和社會生活。
“國學”是一門中國本土的學問,主要是研究中國古代的經典。這當然是很必要的,但是要把它視為全面瞭解歷史中國的學問,我認為欠妥。
全面和深入研究中國的學問,最恰當的名稱應該就是“中國學”。現在在歐美,使用最廣泛的概念也是“中國學”。“中國學”本身也包含了“漢學”和“國學”的研究。歷史中國必須是放在世界範圍來研究,不然就無法真正瞭解中國,所以“中國學”到了今天,成為“世界中國學”,並且很好地將上述三者融合起來。
中國學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,如果只是中國學者關起門來閉門造車,不可能提出很多對世界有影響的學術成果,外國學者也一樣,所以必須交流。研究中國的時候,不管是用哪一種方法,只要是用功的、認真的,研究結果對認識中國有幫助,就有裨益。
中新社記者:您認為歷史中國和當代中國之間有何聯繫?
李伯重: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·諾斯(Douglass North,又譯作“道格拉斯·諾思”)曾說“歷史是連接過去、現在和將來的一座橋樑”。“我們從哪里來”和“我們將來要到哪里去”是連續的過程,而不是過程的斷裂,不能把歷史中國和當代中國割裂開來。現在學術界越來越多的人都認識到這一點。
相當長的時間裏,中國史一直處於較為邊緣的位置。20多年前,學術界出現了一個重大事件:美國加州學派提出了“大分流”理論,引起了世界反響。當時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教書,一批在加州各大學任教而且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學者經常會面,探討中國史研究方面的問題。大家有很多共同的想法,都力圖重新看歷史上的中國,特別是明清的中國。我們都認為當時學界流行的“中國停滯論”或者“衝擊—回應”模式有問題,因為中國有其自身發展的動力。“大分流”後來變成一個國際學界熱烈討論的重大課題,至今仍討論不斷。
到了今天,我們越來越認識到歷史和現在是割裂不開的。大家都在說的中國特色,就是我們國家長期的歷史發展所形成的特點,歷史給我們奠定了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國情,我們的現代化也必然體現出中國特色。如今,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一點,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。
中新社記者:漢學家在理解中國文化上面臨哪些困難?
李伯重:首先是語言的困難。我最初到海外時,主要和漢學家打交道。一個漢學家,要能夠閱讀中國的古文,需要大量時間。許多漢學家對中國沒有身在其中的直接瞭解,只能是從書本上瞭解,這就局限了他們的認識。海外漢學是傳教士奠基的,他們留下的關於普通人的記錄極少,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,是無法研究歷史的。
現在我接觸到的海外比較年輕的中國學研究學者,他們的中文水準都不錯,特別是口語相當好,只是看古文還比較費力。
研究中國歷史強調個人的感受。比如研究唐史,就需要沉浸在唐代的語境中,這樣會比較容易理解很多東西。讓研究中國的學者到中國來實地體驗,是必需的。
中新社記者:研究中國學的學者該如何保持應有的學術性?
李伯重:不管西方人還是東方人看中國,中國就是中國。但從不同視野、不同角度來看,可以看到中國的不同方面。
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跡,到底為什麼會成功?是什麼導致我們在經濟發展中遇到了很多困難?這都是需要研究的。儘管各國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,但真正能夠找到符合中國國情的答案,還要靠大家的合作,特別是要靠我們自己的深入研究。
我們的研究要讓人家懂,讓人家接受,必須用大家都懂的方式。這不單指是否使用英語的問題,而是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都得讓人聽得懂、看得懂、能理解。我研究中國經濟史,特別是從明朝到清朝的長三角經濟,西方學者或許不了解這個地區的歷史,但能理解我的研究方法。我提出的是新觀點,他們也覺得觀點很重要。
多視角是認識自己的一個重要方面。我認為,把各個視角看到的不同方面融合起來,才是一個全面的中國。如果世界中國學將來發展得好,能夠讓學者之間更加密切合作,這肯定是件大好事。
中新社記者:隨著逆全球化思潮進一步蔓延,全球範圍內的國際交流和交往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。能否從過去世界發展的歷史經驗中找出應對現狀的智慧?
李伯重:歷史上人類交往活動的形式多樣,只有貿易交往基本上是持續不斷且以和平的方式進行,因為商業的特點是經過協商達成共識,進而完成交易。18世紀以來,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自由貿易是正確的政策,借此能夠得到與靠征服或佔領獲得同樣的收益,而且貿易往來降低了國家間爆發衝突的概率。
歷史的進程證明,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。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,主要方向是會提高整個世界的經濟總量,從而造福於世界各國人民,但是它也會改變世界經濟格局,讓原來的優勝者逐漸被拉下來。在此背景下,得利有多有少,就會出現矛盾。歷史上沒有先例解決這個問題,但全球化的趨勢不會改變。
這股“逆流”也提醒我們,中國必須持續推進產業升級,提振內部消費,更要加強對人民的福利。先把自己的“內功”做好,等到“逆流”逐漸過去的時候,才有更大的爆發力。(完)
来源:中新社